8月11日,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,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、乔叶的《宝水》、刘亮程的《本巴》、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东西的《回响》获奖。记者第一时间联系采访获奖作家,倾听他们的获奖感受和创作初衷,畅谈如何用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呈现中国大地上的万千气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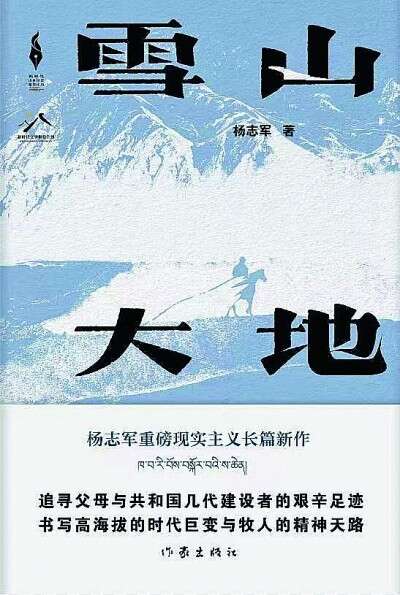
听到获奖的消息时,杨志军正在青海采风。尽管由于工作关系,他搬出青海很久了,但是年年都会频繁地回到这里,跟大哥聊聊天,随处走走,看看他们的新生活。
“能获得茅盾文学奖,我非常激动,这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,是读者、文学界同仁对我创作的一次极大肯定。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特别感谢青藏高原这片故土,是这里培育了他,孕育了他的文学之梦。“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部作品,将自己的感恩之情讲给这片土地听。”
杨志军在《雪山大地》中,深情回望了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足迹,书写了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。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,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。
谈及《雪山大地》的创作初衷,杨志军坦言,他最初想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,写一户汉族人和草原牧民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相濡以沫的交往。“但一动笔就发现,这不仅是我的故事,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,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、洒下血汗、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。”
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。他的父亲,作为一位从洛阳来到西安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,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西宁,在一家马车店里创办《青海日报》。母亲当时还在求学,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,便立刻报名上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,后来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。
在那些年月里,年年都有“西进”的人,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建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、第一所医院、第一家商店、第一个公司、第一处定居点、第一座城镇。“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,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演绎成荒丘的生命,并在多少年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。”
杨志军出生在青海,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。对他来说,那片高海拔的山原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。“创作《雪山大地》,就希望通过我和我的父辈们的生活,让人们看到那些恒久不变的高海拔的冻土带上,有着怎样的温度和爱的氧气。”
2022年,《雪山大地》作为中国作协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首批重点作品发布。对于乡土文学创作,他认为不能以一种“离乡者”的姿态书写记忆里的乡村,而要实地去体验和感受。
在西宁,杨志军住的小区里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,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,如今在城里开着汽车到处跑。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瓜果进出小区,杨志军都会高兴地说一声“乔得冒”(你好),脑海里还是会浮现当年牧民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时的情形。“现在出门就是大超市,对他们来说,那就是一个可以便捷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。”
当然,发生明显的变化的不光是生活,还有那些可以左右生活的观念和意识,以及与他们相伴的雪山大地。“我希望雪山大地的变化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,希望在我讲述父辈和同辈的故事时,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流连忘返,希望绿色之爱也是人心之爱,在广袤的河源厚土上,袒露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传承。”
获奖是一次新的起点、新的出发。杨志军正在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,主题仍是他深爱的土地。“身心的融合、情感的投入、精神的一致,这是最重要的,再加上知识,都是写作所必需的。热爱自己的故乡,热爱一个民族,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搞深搞透。”他将一如既往地行走着、思考着、书写着。


8月11日,悉如平常,刘亮程带着几个学生在新疆木垒书院干活。前日,刚在院中造了一座小景,他的心情甚是愉悦。听到获奖的消息时,心情反而比较平静。他最先想到的是感谢:“感谢新疆这块土地上丰富绚烂的多民族文化生活给我的滋养,感谢并致敬蒙古族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,我的小说《本巴》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,在史诗尽头展开一个现代作家无尽的想象。”
他在新疆生活60多年,深受这里多民族文化的滋养。“一个作家对土地的回馈,可能就是写成一部书,让曾经活着的人们,在文字的世界里永久地活下去。以虚构之力,护佑延续这样一个世界的真实。”
说起创作的缘起,还要回到十多年前。那时,刘亮程前往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旅行,这是英雄江格尔的故乡。该地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,“羊道遍布每一片山谷草原,那是羊走了几千几万年的路,深嵌在大地”。他深受震撼,跑遍草原和山区,认识了许多牧民。
自那时起,刘亮程开始读蒙古族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,他念念不忘这片草原。他感动于史诗的天真带给部落的希望与力量,感慨于人类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象。自此,他萌发出一个念头:“写一部天真的小说。”
“江格尔的本巴地方,是幸福的人间天堂。那里的人都二十五岁,没有衰老没有死亡。”这是《江格尔》中的句子。而《本巴》就以《江格尔》为背景展开,构想出一个没有衰老、没有死亡,人人活在25岁的本巴国度。在史诗驻足的地方,追溯逝去的人类童年,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诗性智慧,向世界讲述古老而新奇的中国故事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孩子,写了三场游戏,两个国家,写了人们在无穷无尽的睡着和醒来里,开始的无边无际的梦和冥想。
《本巴》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。“我把时间作为一个本质,而非手段去写,写出时间的面貌。”事实上,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,母题就是时间。他曾说:“我希望我的文字最终展现的是一张时间的脸。”无论是早年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写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还是后来的小说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,都与时间息息相关,《本巴》更可谓一部在时间中任意穿梭的奇幻小说。
“写作是用文字徒劳地垒筑终将溃塌的时间之坝。”刘亮程有个执念,那就是时间虽然不可战胜,但作为个体,他至少还有时间去抵御,把自己精心选择的事物留在文字中。他相信好文字会活下去:“那些把时间兜住的文字,总会让我们有片刻的会心与停留。”
采访最后,刘亮程向记者透露:“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也快收尾了,几乎是跟《本巴》同时写的,《本巴》先写完了。我的每一部长篇都是自己生命阶段的结果,不到这个年龄写不出来。就像《本巴》,它在我心中生长了十多年或更久,起先只是一个念头,它长成一个大故事了,就是我动笔书写的时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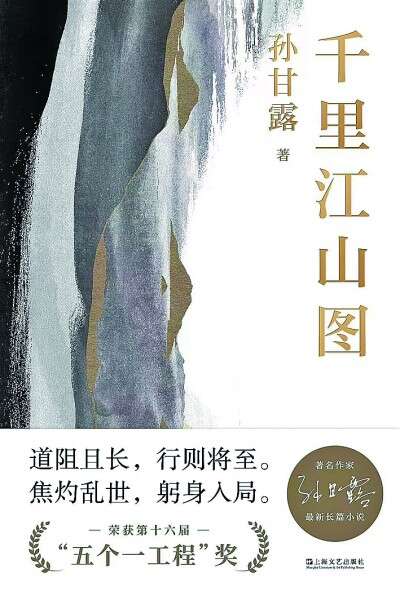
“因为在上海作协工作,我接触过很多获茅奖的作家作品,今天能和这么多优秀作品一同参评,已经是莫大的荣幸。”听到《千里江山图》获奖的消息,孙甘露想到,他的小说发生年代是1933年,而那年茅盾先生发表了《子夜》。“我想正好借这部作品向前辈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!”
孙甘露是地道的上海人,从没离开过上海。“《千里江山图》写的也是上海的历史,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。作品能够获奖,也是对这座城市的回馈。”
《千里江山图》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,以陈千里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,面对和生死考验,以忠诚与信仰、勇毅与牺牲,在危机四伏的隐秘战线上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,成就了惊心动魄、震撼人心的红色传奇。
最初有创作想法,是在20多年前。当时孙甘露和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包括画家,在一起聊天,说起了绘画史的掌故。有历史上的、传说中的,也有关于上海的。里面有些内容,他后来还写到小说里去了。“但是具体要写什么,我没想清楚。”
后来有一个契机,让他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秘密转移行动——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。“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多里地。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,必须绕道,这样的线里地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。”
一次机密的行动,也是一次返乡之旅,一次对未来的展望之行。孙甘露通过小说的叙事旅程回溯时代的风貌,通过街巷、饮食、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,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,对大变革时代的拥抱和体悟。
孙甘露曾写过《信使之函》《访问梦境》《我是少年酒坛子》等,被文坛视作“先锋派”的代表,而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次新的尝试。小说的题材、人物塑造、叙事方式都呈现了很大的变化,从扑朔迷离的先锋叙事转向了朴实平整的现实叙事,为革命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。孙甘露坦言:“我把自己视作一个初学者,一个新作者,实际上也确实如此。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,从头至尾将其视为一次全新的学习过程,既是对历史的辨析,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。”
正是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,他重新认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、中国文学的传统,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,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同时,为了让细节更具说服力,孙甘露广泛搜集党史早期史料,深度挖掘龙华革命烈士生平事迹,查阅参考当时的城市地图、报纸新闻、风俗志等档案材料。一条马路、一件大衣、一出戏、一部交响曲、一道菜……建构出身临其境的空间感。
创作从未止步。孙甘露透露,他目前正在翻阅一些史料,也有些不成熟的构想,希望将来有契机变成一个成熟的故事,呈现给读者朋友们。


在五十岁这一年,乔叶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。这并不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,却被她视为自己的“长篇突围之作”。因为这一次,她坚实地把作品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。
《宝水》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文字书写豫北一个叫“宝水”的山村的四时风物与日常生活,以丰富而扎实的细节展现传统风俗中悄然发生的山乡新变。小说以平实生动、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语言,通过对乡建专家、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等经典人物的塑造,为中国大地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。别有意味的是,乔叶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起名为“地青萍”,赋予其土地的底色。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,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,自身的失眠症被逐渐治愈,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。
乔叶出生于河南修武县,在乡村度过了童年岁月,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乡村教师,有比较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。对很多喜欢散文的读者来说,乔叶这一个名字不会陌生。在20世纪90年代,乔叶就因其优美的散文深受读者喜爱。在进入河南文学院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后,乔叶又重点在小说创作领域勤奋耕耘,硕果累累。2010年她凭借《最慢的是活着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,这部作品对乡村女性生命进行了有力的书写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乔叶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作。2020年,乔叶调到北京,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。
“我特别想要感谢的是两个地理概念:感谢老家河南,感谢新家北京。”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,乔叶首先想到的是“感谢”。“《宝水》写的是河南的乡村故事,最基本的体验和感受都来源于河南,而北京三年的生活和工作对我的写作很有重要的提升和成长。如果说《宝水》里面的情感基因是河南,那么《宝水》背后的精神气场就是北京。”
“我更要感谢这个大时代。大时代让我享受到了多重福利,非常幸运。”乔叶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:今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她关于《宝水》的创作谈《精神原乡的返程》,这天的光明日报综合新闻版正好刊发了她老家的消息《河南修武:春回云台旅游旺》,和创作谈简直是相互呼应的“美好邂逅”。据这则新闻报道,云台山镇“发展民宿和家庭宾馆373家,民宿集聚程度在全省首屈一指”。“在这些家庭里,想来都有些《宝水》故事。《宝水》的创作,就源自这些人家的故事。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故事。”乔叶感叹道。
在七八年前乔叶有了想要写《宝水》的意念后,便开始了她称之为“跑村”和“泡村”的前期准备阶段。江西、甘肃、贵州等地的村庄“跑”过,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、温州等地很富庶的村庄“跑”过,河南的如豫东、豫西的村庄也“跑”过,她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。“泡村”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,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、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。在体验阶段过后,她进行了知识补充、人物采访,还有情感投入,克服了创作上的重重困难,一字一句,点点滴滴,慢慢写起,涓涓汇聚,终成了这部《宝水》。
乔叶认为,作家的写作必然在时代中,无论多么个人化的写作,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化写作。“作家和时代,就是浪花和大海、庄稼和土地的关系。弱水三千,取一瓢饮,这一瓢水也是时代的成分。在这个大时代里,我很幸运地取到了属于自己的《宝水》,充满了感恩。”


1966年出生的作家东西,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,在大学读书时便开始发表诗歌、散文及小小说,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担任语文老师,其间,他的写作从未间断,直至成为一名专业作家。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,奠定了他在文坛的位置。
在20世纪90年代,东西与毕飞宇、李洱、邱华栋、徐坤、艾伟等作家一道,被文坛命名为“新生代作家”,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表达现实关切之外,也注重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。如今,这批“新生代作家”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。在获知得奖消息后,东西在激动之余感到,这份殊荣首先来自文学界对“新生代”这个作家群体的肯定,是对一种严肃文学探索的肯定。
《回响》这部获奖作品让读者阅读起来很有快感,它借助了侦破、悬疑等类型文学元素,为此东西补习了刑侦学和心理学的知识。某一种意义上,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。小说塑造了一位女警察冉咚咚,她以其敏感、细腻和多疑的缜密思维,一而再地破解案件的迷局,同时也战胜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,最终以超人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将凶手绳之以法。
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《回响》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,小说采用双线结构,与现实中的追凶破案并置的另一条线索,是女警官冉咚咚对丈夫——文学教授慕达夫是否情感不忠的侦查,相比前一条主线,这条两人之间的心理战更为内在,也更具张力,充分体现了小说家东西的语言艺术、叙事才华和透视人物内心的能力。用作家韩少功的话说,东西小说中那些“呼啦啦喷涌”而出的“坚实的细节”,使他的小说“全程紧绷,全程高能,构成了密不透风和高潮迭起的打击力”。
《回响》中的人物在幽暗中反复摸索,结尾却为读者留下了一道亮光,这是作者本人最为看重的:“我的内心太需要光了,尤其在各种考验面前。冉咚咚经历了那么多考验,如果没这道光,那她的追求就会毫无意义。过去我喜欢悲剧的结尾是相信希望孕育在绝望之中,现在我喜欢光明的结局是因为害怕黑暗。”
东西是文学界较早“触电”的作家之一,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。这部《回响》也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网剧,已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与广大观众见面。
“获奖不是终点,而是激励和鞭策,鼓励我继续前行。”东西自勉。从1995年的《耳光响亮》到2005年的《后悔录》,从2015年《篡改的命》到近年的《回响》,东西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从始至终坚持艺术创新。“作家变来变去都是在写自己,写自己的内心,写自己对世道人心的理解与不理解。不变的是,我一直注意创作跟现实的紧密关系,注意小说的可读性和细节的准确生动,并努力追求语言的新颖。”
东西出生在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八腊瑶族乡洞里村的一个农家,他此次获奖,也实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茅盾文学奖上“零的突破”。“荣获茅盾文学奖,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,也是对我们广西作家的一个鼓励,尤其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鼓励。”东西认为,广西大力扶持文艺精品创作,注重广西特色文化品牌建设,使本区文艺创作不断拓高原、攀高峰。